北宋第一实干家: 文能治国, 武震契丹, 才胜苏轼, 不应被历史遗忘
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,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,请知悉。
前言:
在朝堂上,章衡面对宋仁宗提问西北边防该如何治理,只用了一句就震惊四座。
此时苏轼尚在考场外候考,而这位新科状元,已在殿前纵论军政。
他文能治水反腐,武能百步穿杨震辽主,才具不输苏轼,却成了被历史尘封的实干家。

宋仁宗庆历年间与西夏的战争虽暂告平息,但西北边境仍常年驻军数十万,军费消耗占国库收入的六成以上。
年轻的章衡敏锐地察觉到,单纯的军事对抗只会拖垮财政,他在殿试中提出的实边策略,包括充实边境粮仓、推广屯田、修缮城防。
这种思路在当时并不主流。
朝堂上,主战派仍主张犁庭扫穴,主和派则倾向岁币换和平,章衡的中间路线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
但他并未放弃,第三月便主动请缨出使辽国,实地考察边防虚实。

辽道宗耶律洪基对这位宋朝新科状元早有耳闻,设宴时特意设下武试环节,席间辽主指着百步外的靶心说,
听闻南朝士子只会挥毫,不知能否挽此强弓?
章衡放下酒杯,接过辽兵递来的铁胎弓,此弓拉力超过一石五斗,寻常武将也难拉开。
他深吸一口气,左手如托泰山,右手似抱婴儿,三箭连发,箭箭穿透靶心红圈。
辽主席间的笑声顿时变得勉强起来,章衡趁机提议互观边防。

在辽国境内考察时,他看似随意地记录山川走向、关隘分布,归国后连夜绘制《燕云山川图》,建议趁辽军主力西调平叛之机,收复山后八州。
然而此时的宋仁宗已近晚年,朝中重臣多求稳怕乱。
宰相富弼认为边境初宁不宜轻动,章衡的奏折被束之高阁,而十余年后辽国平定内乱,宋朝再无收复良机。
章衡只得改任地方官,首站便到了真定府。
这里常年被洪灾困扰,历任官员要么筑堤堵截,要么听任水患蔓延,始终没能彻底解决问题。

章衡到任后,沿河岸徒步勘察三日,终于发现症结:河道中游因泥沙堆积形成卡口,使得水流阻滞不畅,他提出的束水攻沙之法。
施工时,有老河工质疑水势若太急,恐冲垮堤岸,章衡就让人在堤岸内侧加筑防冲棱体,既保证了流速,又保护堤基,百姓称之为章公堤。
治河功绩未让章衡止步。
调任澶州时,他遇上更棘手的难题,官盐专卖导致盐价飞涨,百姓被迫用野草熬盐充饥。
按宋朝制度,盐价由三司统一制定,地方官无权更改,章衡却在州衙门前贴出告示表示日起开放盐市,官仓盐平价发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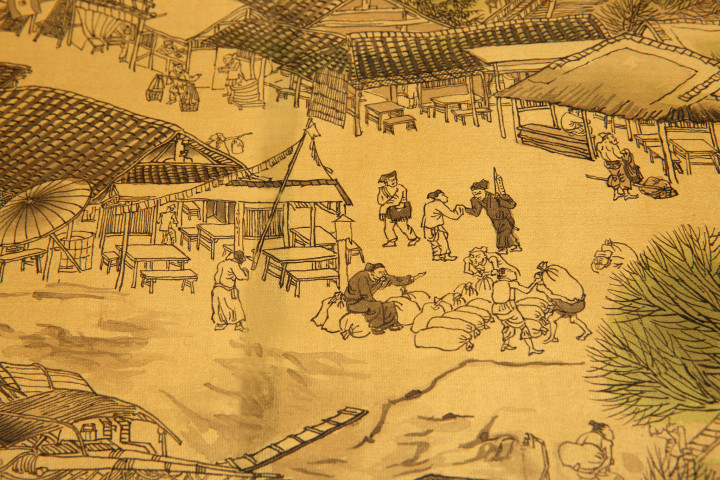
这一举动震动朝野,三司使弹劾他擅改祖制,章衡在奏折中据理力争:
澶州现有二十万口,官盐每斤百文,百姓日食需盐五钱,而农户日收入不足三十文。
开放七日,已售盐五千斤,无人饿死;若再禁售,不出十日将有流民。
宋仁宗看后沉默良久,最终同意了他的做法。
除此之外,章衡也帮了苏轼不少忙,他们虽同科及第,却分属不同政治阵营。
章衡务实不喜空谈,苏轼则长于文辞,一度卷入新旧党争,但私下里,他们却相互敬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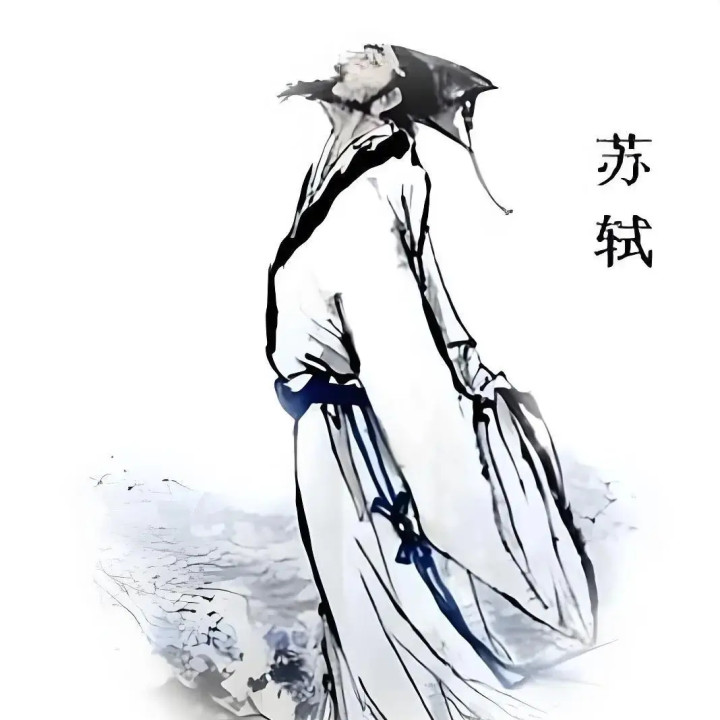
当年苏轼因西湖湖底淤积过深束手无策,便致信章衡求援,章衡当即调派驰援,还建议将淤泥堆筑成堤,把湖面分隔为二,这条长堤便是后来的苏堤。
然而苏堤落成后,碑文中竟未提及章衡的功绩,章衡对此类幕后功绩似乎毫不在意,他在地方任上政绩颇丰:
在扬州修复芍陂,使万亩农田得以灌溉;在成都改革茶法,通过降低茶价惠及百姓,只是这些举措仅在地方志中留有零星记录。
章衡的历史地位之所以被低估,与其处世风格直接相关。
北宋中期党争渐起,士大夫多依附王安石、司马光等权臣,章衡却始终保持独立立场。

他的实干作风也与当时的官场风气格格不入。
北宋重文轻武,士大夫大多以诗文见长,章衡却潜心研究工程、财政等实务,这在当时被视作功利之举。
更重要的是,章衡拒绝参与官场应酬。
他任礼部侍郎时,同僚们常聚在一起吟诗作赋,他却总以有公务为由推脱,转而研究各地的赋税账簿。
不合群的性格使得他在史书中的记载寥寥无几。
章衡的一生,恰如他主持修筑的堤坝,不事张扬,却能抵御洪流。

在北宋那个充满理想主义与党争的时代,他以务实精神在边防、水利、民生等领域留下了扎实的业绩。
与苏轼的文名远扬相比,章衡的功绩或许不够耀眼,却更贴近治国理政的本质。
历史不应只记住那些文采风流或权倾一时的人物,像章衡这样默默做事、造福百姓的官员,更值得被铭记。
参考资料:
《宋史・章衡传》(脱脱等撰,中华书局标点本)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(李焘撰,中华书局,2004 年)
《苏轼文集》(中华书局,1986 年)
《正定府志》(光绪年间修,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3 年)
《北宋边防策略研究》(王曾瑜著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7 年)
《宋代水利史研究》(魏天安著,河南大学出版社,2007 年)
《章衡与北宋中期政治》(《史学月刊》2005 年第 8 期)

